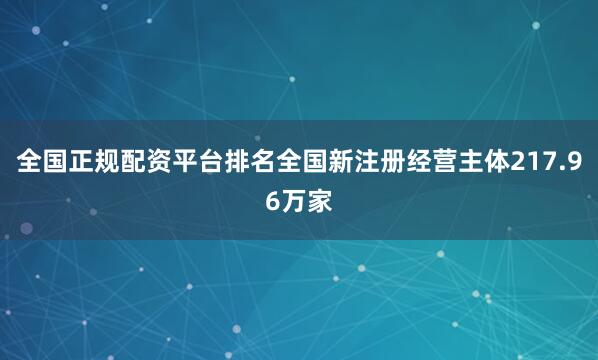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阶段,各级官员在生活中享受的等级化特殊待遇已演变成一种制度,其核心便是“地位决定一切”。正如叶利钦在其自传《我的自述》中所述,莫斯科大约有四万人享有各种特供商品,而这些待遇亦分等级。至于部长级,尤其是政治局委员,叶利钦将其形容为“攀登至党的权力金字塔之巅”,届时他们便能享有所有特权,“仿佛迈入了共产主义”。

在一座宏伟的豪宅中,四十至五十名仆役忙碌地为一家服务,日日有亲朋好友及食客络绎不绝。这样的场景若与亿万富翁或皇族贵族的宅邸相比,或许并不令人惊讶。但当这一幕与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生平交织在一起,又会引发你怎样的遐想呢?
1935年,法国知名的文学家罗曼·罗兰访问了莫斯科,并在其《莫斯科日记》中详尽记录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。他笔触间流露出深深的惊讶:“那些身为国家和民族守护者的英勇战士及其领袖,正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独特的阶级”,“而广大民众,依旧为了求得一块面包、一缕清新的空气(即住所)而陷入艰苦的挣扎”。罗兰更是震惊地发现,连无产阶级的杰出作家高尔基也沦为被贵族般供养的对象。在他看来,苏联已悄然兴起了一个“特殊特权阶层”与“新兴贵族阶层”。
特权阶层的形成,源于制度的精心设计。斯大林凭借其手中的“无限权力”,尤其是对干部分配的掌控,创设了官职等级名录制度。1923年11月8日,俄国共产党(布尔什维克)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项重要决议,正式确立了选拔与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完整体系。该决议对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任职资格进行了明确规范。在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,涵盖了约3500个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,其中不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的首脑、托拉斯与辛迪加的领导者,以及大型工业企业的负责人;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则包括了各部、局的副职及其他相应职务;而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,则专注于地方领导干部的选拔。
若你得以荣登名录之列,便意味着你已被纳入特定的安排之中,从而得以领略特权阶层的优越生活。
若你目前尚未名列其中,不妨着手寻求对策。
截至1924年年初,中央委员会正式确定的领导干部人数共计13,163名。各地各级党组织亦各自设定了官职等级的清单,例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地区领导干部的人数为1,066人。然而,地方领导干部的任命中,仅核心职位需由中央委员会直接决定。
官职等级名录收录了最为关键的职位与职务,而人选均需由中央委员会预先审查并予以批准。即便解除职务,亦需中央委员会的许可。斯大林居于这个权力金字塔的顶端。
权力持续汇聚。联盟的部级机构增至160个,而各个行政部门所颁布的法律与命令法规种类已逾20万,条款多达千万,甚至可以说是连如厕这样的小事都有详细规定。行政指挥体系虽得以强化,却缺少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,这无疑导致了国家机构的膨胀与官僚作风的盛行。至1985年,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副部长人数已超过800位,一份普通文件的审批往往需耗时数周,有时甚至长达一两个月。
官职等级名录,随后,这一概念演变为一个专有名词,有幸跻身其列的苏共领导干部逐渐蜕变为所谓的“红色贵族”——一个拥有个人利益、生活方式及意识形态等特殊属性的社会阶层。
特定工资制和“钱袋”制
在斯大林时期,苏联共产党高级干部享有的一项显著特权便是特定的薪酬制度。1945年4月,苏联政府正式实施规定,对于在机关、企业或团体中担任关键职务,并具备深厚学识与丰富经验的人员,将实行特殊的薪酬制度。该制度的薪酬范围通常设定在2200至3000旧卢布之间,而最高额度则可达到4000至5000旧卢布。
该特定薪资数额随后再度攀升。然而,这一增幅并未在工资条上明确标注,而是随同薪资一同装入密封的小纸袋中发放。这便是苏共历史中所谓的“钱袋”机制。
在1969至1986年间,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苏联作家丘耶夫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。在这些对话中,他们探讨了一系列话题,其中便涉及到了薪酬及所谓的“钱袋”制度。莫洛托夫透露:“我现时难以确切告知您我的具体薪资,因为它已经经历了几次变动。此外,战后,应斯大林的提议,我们实行了‘钱袋’制度。通过封装严密的小包裹,向军事和党的领导人输送大量资金。当然,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恰当。金额不仅过于庞大,而且过于夸张。对此,我并不否认,因为我没有权利对此提出任何异议。”
现金被巧妙地封装于信封之中,秘密地分发给各级官员。每月的金额,通常根据官员的职务高低,介于几百至数万卢布之间(以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换算为新卢布的比率为101)。这些资金无需缴纳任何税费,甚至党费中也未曾包含在内。那些接受“信封”的人,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,任何泄露消息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。在扣除通货膨胀和币制调整的影响后,在斯大林统治时期,一位部长每月的“秘密津贴”约为2000新卢布,这笔钱相当于3500美元,几乎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薪的一倍还多。而与此同时,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,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,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800美元。
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政策进行了否定,并毅然决然地着手改革干部特权体系。他力主实施领导干部轮岗制度,并对高级官员的薪酬进行了裁减。1957年2月,苏联方面曾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通报,苏联将从3月1日起对高级官员的工资进行调整。在最新规定中,政府部长的月薪上限定为8000卢布(按旧卢布计算),副部长的月薪则为7000卢布,而部务委员的月薪标准为4700卢布,司长为4500卢布,副司长的工资则在3000至4000卢布之间。党中央各部的领导层工资也有所下降,但较政府部门官员的工资略高。此次降薪的幅度相当可观。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为例,其工资从原本的15000卢布降至5000卢布。与此同时,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仅为300至350卢布,即便是在高官降薪之后,他们的收入与普通民众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。
赫鲁晓夫的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,反而导致了其政治生涯的终结。
位居官阶显赫之列的权贵们,纷纷拥护废黜赫鲁晓夫,力推勃列日涅夫登基。勃列日涅夫迅速对赫鲁晓夫的统治予以否定,他采纳了全然依赖特权阶层的策略,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世袭性,对领导干部的轮换机制进行了改革。他不仅恢复了赫鲁晓夫曾废除的部分高级干部的特权,更是增添了一系列新的特权。
根据现有资料,前苏联的顶尖高层领导在物质享受上无疑是“应有尽有”,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薪酬差距甚至超过五十倍。此外,任何机关领导干部每月都能获得超出工资一倍以上的额外补贴,且职位越高,补贴金额也越丰厚。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,苏共政治局的成员已各司其职,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苏联首都莫斯科。每当周末来临,位于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便会上演一幕奇异的景象:一排排擦得发亮的“伏尔加”轿车整齐排列,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。司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后视镜,对交通规则和警察的警示置若罔闻,随意地将车辆停放。他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楼的入口处。

小白桦商店
这栋土黄色的建筑,其窗户透不进光线。门旁悬挂着一块标牌,上面注明1919年,列宁曾在此发表过激昂的演说。另一块标牌上则赫然写着“领证处”。然而,并非任何人都能踏足此地领取证件,仅有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方具备这一资格。男女宾客手持大提包,登上汽车,扬帆远去。他们皆系苏联上层精英,专程莅临这座无任何招牌、仅凭特殊证件方可入内的神秘商店,选购所需之物。
众多秘密商店专为苏联的精英阶层服务,向那些“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”敞开大门。这些特别的店铺里,上层人物得以购得苏联国内难得一见的美食,诸如鱼子酱、蝗鱼、鲑鱼以及出口级伏特加,同时还有诸多“资产阶级”的奢侈品,例如法国白兰地、苏格兰威士忌、美国香烟、瑞士巧克力、意大利领带、奥地利皮鞋、英国呢绒、法国香水、德国晶体管收音机和日本录音机等。
这正是令莫斯科寻常百姓羡慕不已的“小白桦”商店。
位于莫斯科最大国营百货公司“古姆”三层的一隅,藏匿着一家名为“100号分店”的神秘场所,该店专为广大上层人士量身打造。而在军人商店的地下室深处,则设有仅供军官使用的隐蔽商店。此外,全市范围内遍布着众多为特权阶层量身定制的特殊裁缝店、特殊理发店、洗衣店以及化学洗染店,各类食品店亦不计其数,总计约有百余家。
苏联某位记者曾言:“对上层人士而言,共产主义建设早已宣告完成……”
这正是苏共高级干部所享有的特殊待遇。为了保持这种特权,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
苏联昔日赫赫有名的“首都”伏特加,正是在德军围城、粮食资源极度紧张之下的列宁格勒制造而成。
1942年,德国军队将列宁格勒团团围困,犹如铁桶般严实。城内居民困顿于饥寒交迫之中,饿得步履维艰,宛如“活着的幽灵”。在这严峻时刻,列宁格勒知名的酿酒师斯维德利,在酒厂的实验室中辛勤劳作,挥洒汗水,遵照上级的神秘指令,精心酿造“首都”牌伏特加。
那珍贵的谷物被精心酿制成风味独特的美酒——这并非对抗法西斯的神秘武器,而是专供军队高级将领和市委领导阶层享用的“特制佳酿”。
若将此等粮食节约下来,或许能够挽救无数市民的生命。
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前任所长阿尔巴托夫,在其著作《苏联政治内幕——知情者的见证》中,深入探讨了斯大林时代盛行的特权体系。
他笔触间流露,“按照该制度的层级划分——政治局委员、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书记、中央委员、人民委员,以及各局的首领们,每一层级皆享有各自的特权。战前,享有这些特权的人群规模有限,然而,所获得的特殊待遇却极为丰厚。”随着战后的配给制被废除,特权阶层迅速膨胀。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,各级官员均能享受到黄金地段的高级住宅、免费使用的别墅、专属汽车(包括领导人和其家人,有时甚至拥有一人几辆可供选择的车辆)、专职司机、免费的早餐与午餐、假日疗养的资格,以及大量路费、补贴和所谓的“医疗费”。此外,他们还享有豪华的狩猎活动,无需排队即可在特供商店购买紧俏商品和进口奢侈品(仅莫斯科就有数百家此类商店),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特殊供应。
自70年代起,苏联的特权阶层规模日益膨胀。
供应特权阶层的体系是按照等级划分的。最顶级的供应自然属于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,他们享有所谓的“克里姆林宫份额”,能够享受到众多免费的物资。在莫斯科,设有专为1930年前入党的资深布尔什维克设立的配售点,还有专为元帅、将军们设立的特殊配售点,以及为知名学者、宇航员、社会主义劳动英雄、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准备的平价配售点……这些按级别划分的商店,相较于普通商店,商品种类更为丰富,价格也更加公道。此外,还设有专门的服装店、理发店、食品店等,为特权阶层提供专属的供应与服务。例如,莫斯科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上的内部商店,专门为高级干部提供紧俏商品;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内设有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区,仅限于政府副部长、州委书记、大城市市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官员购买商品;而中央百货商店的45号售货部则是为较低级别官员购物而设。众多政府机关向官员发放“特殊配给卡”,此卡不仅是进入特殊商店的凭证,还标明了可购买商品的金额,级别越高,可购买的商品金额也越多。除此之外,“小白桦”商店出售低价的进口商品和市面上稀缺的物品,仅限持有“卢布证券”的人士购买。所谓的卢布证券,是指通过外汇兑换的特殊卢布,只有有渠道的官员、外交官、记者等才能时常获得卢布证券。

叶利钦
在《我的自述》一书中,叶利钦披露的特权现象既严重又具体。苏联解体前夜,各级官员在生活中享有的等级化特殊待遇已经演变成一套制度,“一切皆以官职的高低为标准”。据他所述,全莫斯科大约有四万人享有各类特供商品,且这些特供商品之间还有等级差异。一旦晋升至部长,尤其是政治局委员的级别,叶利钦将其比喻为“攀上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”,此时他们便能享有一切,“仿佛步入了共产主义!”他讽刺地评论道。鉴于当时人们的需求胃口普遍很大,苏联“只能暂时为寥寥数十人营造真正的共产主义”,而“几十个人享受着共产主义式的生活,而广大民众则陷入贫困的深渊”。
利加乔夫,曾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员,在回忆1983年的情景时提及,自他接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之职的次日,便被配备了豪华轿车。然而,当他提出更换一辆档次较低的车时,却意外地受到了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严厉斥责,指责他此举是追求“特殊待遇”,有损机关风气。面对这样的指责,这位新近晋升的高级官员不禁感到惊讶不已。
在1936年,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·纪德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之旅,回国后,他创作了《从苏联归来》一书,书中深刻地揭示了苏联社会的阴暗之处。
首当其冲,高层领导人的生活待遇与普通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高层人士的餐桌上,丰盛的美食琳琅满目,既有各式各样的冷盘,也有火腿、鱼肉——腌制、熏制、冷冻的,热菜则包括虾烧鲟鱼肉、奶油棒鸡等各式佳肴。反观底层民众,他们的境遇又是怎样呢?在阿赫特伦路上,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象:女人们手捧一块垫着草的生肉,站在那里向过路人叫卖,有的则拿着鸡或其他类似物品。她们是无照摊贩,既无财力支付摊位租金,也无需排队等待租用一天的或一周的摊位,一旦遇到执勤人员,她们便手忙脚乱地携物而逃。在莫斯科,大学生、教师和小职员的生活依然艰辛。
苏呼米周边的西诺卜旅馆,乃是高官们款待宾客的场所,纪德对其赞誉有加,认为其堪比法国最美丽、最舒适的沐浴旅馆,堪称“人间最为接近幸福之地”。旅馆旁设有苏维埃农场,专为旅馆供应食材。然而,越过那条界定农场边界的壕沟,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低矮、简陋的房屋。“那里,四人共居一室,屋内长宽均超两米,每月仅需两个卢布的租金。农场所设的餐馆,每餐仅需两个卢布,然而对于月薪仅七十五卢布的他们而言,这样的奢侈实在难以企及。对他们来说,除了面包,一条干鱼便已是满足。”
纪德辛辣地笔锋一转,讽刺道:“这股正在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,继承了——我们旧有资产阶级的种种恶习。它们刚刚摆脱贫困的枷锁,便迫不及待地轻视起贫穷。它们渴望那久违的种种福利,深知如何攫取并巩固其地位,‘这些人’,‘他们是革命果实之享用者’。他们或许名义上加入共产党,然而心中并无半点共产主义者的气息。”尽管苏联那时宣扬全民平等,强调革命战友间的深厚友谊,以及在共苦共甘、共荣共辱中的团结,现实却与这些口号大相径庭。
注释
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:"若你在深夜偶遇某部门灯火通明,切莫误以为他们正埋头加班,多半是在探讨如何将公款化为私囊。"讽刺之处在于,尽管这则笑话言过其实,却与实际情况惊人地相似。到了1925年,贪污案件的数量激增,法院审理工作应接不暇,以至于不得不日夜加班,仍难以应对。
列宁目睹此情此景,愤慨至极,猛地拍打着桌子。随即,他颁布了一项法令,规定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酬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平均水平的标准。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,每月仅领取五百卢布的薪金,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。然而,这些规定如同纸糊的老虎,无法抵挡住腐败的汹涌潮流。
配资炒股评测网,股票配资算非法经营罪吗,人人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