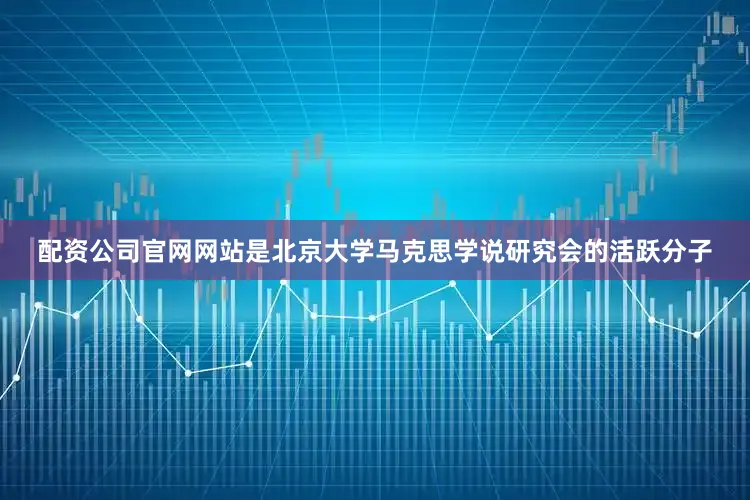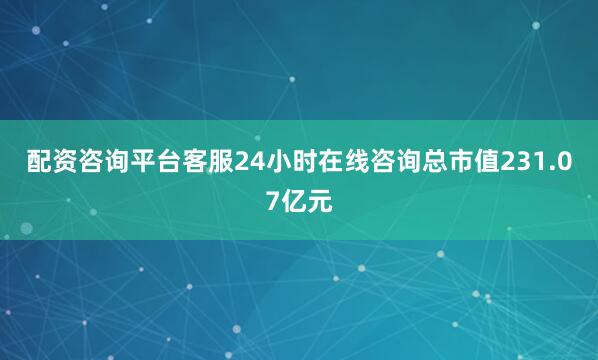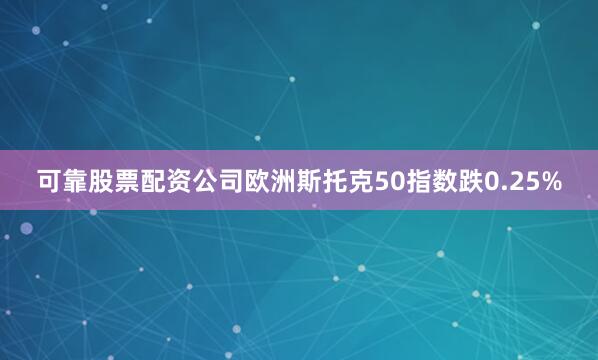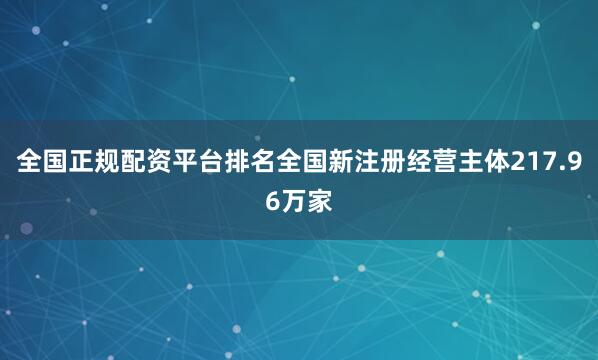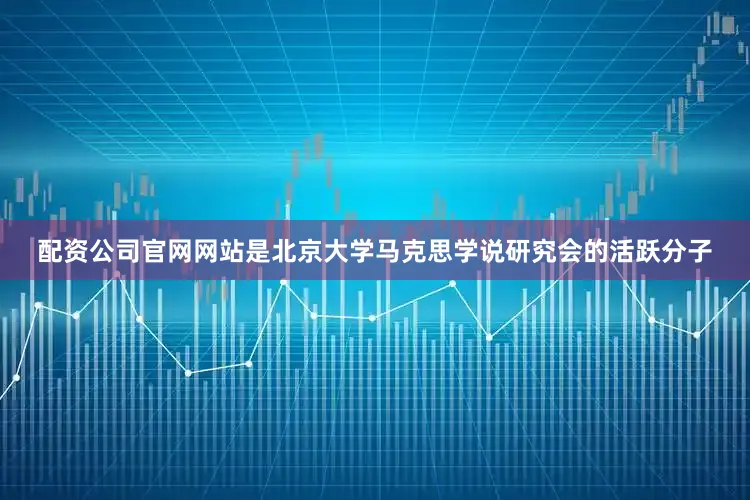
1950年,刘仁静到北京,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。董必武明说不见;李立三辞以不在家;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,谈话不久,秘书就进来提醒吴,说此人不可接触;写信给廖承志,廖不答复。1921年,彼时的刘仁静,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跃分子。在李大钊的指导下,这个年轻人凭借自己扎实的英语功底,啃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英文原著。当很多人还在一知半解地谈论“主义”时,他已经能引经据典,滔滔不绝了。也正因为这份理论上的早熟,在北京支部推选一大代表时,他和张国焘被选中,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秘密旅程。在“一大”的会场上,这个19岁的青年,愣是跟比他大12岁、理论功底同样深厚的李汉俊吵得面红耳赤。李汉俊觉得,当时的中国还不成熟,共产党应该先搞研究、搞宣传,支持孙中山的革命。刘仁静当场就跳了起来,他认为欧洲那种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,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搞武装暴动,建立无产阶级专政。两人你来我往,互不相让。最后,大会的决议,采纳了刘仁静这种更激进的意见。你看,从一开始,刘仁静就不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。他骨子里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,一个坚信革命必须彻底、纯粹,不能有半点妥协的理想主义者。 这种性格,让他早期在党内崭露头角,却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。“一大”之后,刘仁 静被派往莫斯科学习。正是在苏联,他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。当时,苏共内部正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路线斗争,一边是斯大林,另一边是托洛茨基。刘仁静选择了后者。简单来说,托洛茨基主张“不断革命”,认为革命应该在全世界同时发生,并且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体系持批判态度。这种思想,对于像刘仁静这样追求革命纯粹性的知识分子,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他认定,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,而斯大林的那一套,已经背离了革命的初心。这个选择,在当时是致命的。随着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并被驱逐,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清理内部的“托派”分子。1929年,刘仁静回国,因为坚持自己的托派观点,并参与相关组织活动,很快就在1930年被开除了党籍。从此,他从一个缔造者,变成了一个“叛徒”。被开除出党后,刘仁静并没有消沉,而是继续以一个“托派革命者”的身份活动。但在当时的中国,这意味着什么?这意味着他既被共产党视为“异端”,又被国民党当成“赤匪”。他成了一个没有归属的政治孤儿。1935年,他被国民党逮捕,在牢里度过了几年。出狱后,抗战爆发,山河破碎,他却找不到自己的战场。那个他曾为之奋斗的红色队伍,已经将他拒之门外;而那个他坚决反对的国民党政权,更是视他为眼中钉。他只能回到书斋,在北京的大学里教书,做翻译,靠着笔杆子勉强糊口。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,默默地为思想的传播做着贡献。但他心里那团火,恐怕从未真正熄灭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当年参与创建的那个党,在毛泽东的领导下,一步步从弱到强,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。这份心情,恐怕是五味杂陈,难以言说。回到1950年的北京。理解了前面的故事,我们就能明白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背后,藏着多么坚硬的政治逻辑。董必武为什么不见他? 董老是一大代表里,少数几个从头走到尾、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元老。在“一大”上,他就反对刘仁静那种“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”的激进主张,而是提出要联合孙中山,建立统一战线。历史证明,董必武的远见卓识是正确的。在他看来,刘仁静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,代表的是一种幼稚的、脱离中国实际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。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三十年过去了,这个根本性的分歧没有变,见了面又能说什么呢?李立三为什么“不在家”? 李立三自己就曾因为犯过“左”倾路线错误而受到严厉批判。他深知党内路线斗争的残酷。刘仁静这个“托派”的标签,在当时是比什么都敏感的政治地雷。接见刘仁静,无异于给自己引火烧身。一句“不在家”,是最稳妥、也最无奈的切割。吴玉章和秘书的那一幕,则更是意味深长。 吴老或许念及旧情,一时糊涂,想见见这个当年的“小朋友”。但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,已经像一张无形的网,渗透到每个角落。秘书的那个提醒,“此人不可接触”,代表的是整个组织的意志。它告诉我们,在那个一切以政治划线的年代,个人的情感和关系,必须无条件地让位于组织的原则。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,这是一个政治机器运转的必然逻辑。至于廖承志的不答复,那更是彻底的无视,代表着刘仁静在政治上已经被完全“除名”。刘仁静后来的几十年,就在人民出版社当一名特约翻译,在国务院当个参事,拿着一份工资,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他再也没有回到那个他曾经无比熟悉的政治舞台。1987年,他在北京的一场车祸中去世,走完了他这坎坷、矛盾又令人唏嘘的一生。
图片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
配资炒股评测网,股票配资算非法经营罪吗,人人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